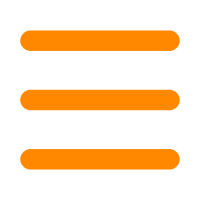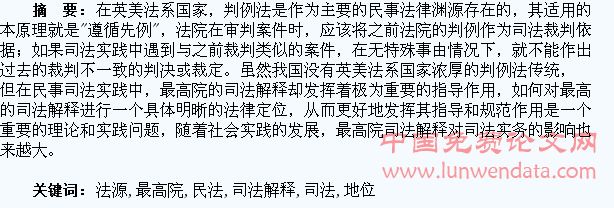
截止到2014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布第六批指导性案例,在所有六批的指导性案例中,每批的民事案件占据了一半或者一半以上,这类指导性案例具备针对性和具体性,为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具体审理案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提升了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统一处置类似有关问题的效率。对于最高院的此类司法讲解,大家应该如何看待它们的地位、审视它们的权威、是不是应该确立司法讲解的作为民法渊源的确定性地位,从而更好地发挥它们有哪些用途是一个极为要紧的问题。
1、最高院司法讲解在司法实践中的争议性地位―可否作为法源
(一)最高院司法讲解在司法实践中成为裁判依据
最高院的司法讲解在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中一直是被适用的审判依据,特别是在具体范围法律适用无明确法律条文可以援引的情形下。最高院司法讲解因其由特定主体最高院作出,而具备了特殊的“身份”,又因这种特殊性而拥有了特殊的法律效力,使得各级司法机关从法理和法律精神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角度出发,格外看重对它们的解析和适用。
正如袁明圣教授所言:司法讲解的“立法化”或“泛立法化”现象已经成为国内司法讲解的一个基本特点和常见趋势i。也有学者指出,法律讲解是中国法律的要紧渊源ii,这其中的法律讲解当然包括了最为重点要紧的最高院司法讲解。毋庸置疑,最高院司法讲解在大家的司法实践中已经饰演着愈加突出的角色,它们的非拟定性法源地位已经得到了切实的体现。
(二)否定最高院司法讲解法源地位的近况
但,那些觉得最高院司法讲解不具备法律渊源地位的呼声也从来没停止过,有的学者觉得,对最高院司法讲解法源地位的认同是对立法权的侵犯和亵渎。国内的有关立法中明确的立法机关并没明确有司法机关,司法机关是作为贯彻和实行法律的机关产生的,各种机关各司其职是依法治国最基本的需要。即使有的法律中认同在具体适使用方法律过程中,确无具体法律援引审理具体案件时,可以作出一些具体有关的司法讲解来使得案件得以审理,但也没赋予这种讲解(其中自然包含了最高院司法讲解)的法源地位,因此,将最高院司法讲解认定为具备何种形式的法源定位都是不科学的。
当然也有学者将这种司法讲解权解析为准立法权,比如梁慧星就是代表iii,还有学者将之认定为习惯法iv,最高院的司法讲解非常显然与习惯法有比较大的差异,将两者混同好像不具备合理性。事实上,在缺失具体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司法讲解确实应该当仁不让,承担起创造性讲解甚至补充规定的职责v。
(三)对最高院司法讲解的界定
法律定义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于司法讲解这一定义而言也是这样,它有两个层面上的界定。广义的界定除去狭义范畴上的司法讲解外,还包含了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及司法工作者在司法实践工作中对具体适使用方法律问题所作出的各种具体讲解,这种广义上的司法讲解一般适用于理论剖析层面。在此文中,大家所指的最高院的司法讲解是从狭义层面上剖析的,具体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针对法律适用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规范的有关问题所进行的讲解。